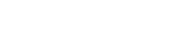用小说法,而以记史
《说史记:小说一样的历史》 杨早 著 后浪|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评《聊斋志异》是“用传奇法,而以志怪”,意思是蒲松龄是用唐传奇的写法,来叙写六朝志怪的题材。同书评唐传奇云:“叙述宛转,文辞华艳,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,演进之迹甚明。”倘以“叙述宛转,文辞华艳”八字来评《聊斋志异》,确实也很贴切。纪晓岚看不惯蒲松龄的地方,怕也在这里:蒲松龄把子虚乌有的事写得太细密、太逼真,不可能是从乡野村老那里听来的故事转述,里面灌注了作者自己无限的想象力。
 (资料图)
(资料图)
莫言说他继承了蒲松龄的传统,论者多集中于研究两人同致力于民间故事的挖掘,而忽略了“叙述宛转,文辞华艳”的一脉相承。其实再溯源头,就该是“无韵之离骚”《史记》。司马迁写鸿门宴,写荆轲刺秦,三翻四叠,动人心魄,实开唐传奇之先河。王小波重写唐人故事,从《甘泽谣》《无双传》《虬髯客传》抓取情节人物,更是将古今熔于一炉。
前面的帽子很大,罗列名家,好像他们跟《说史记》有什么关联。其实没有。我只是想说,有时“故事”(story)和小说(novel)的区别,或许就在于细节之多寡、进程之平曲、想象力之有无。
曾自况《野史记》是“用新闻法,以写掌故”,古今笔记掌故,多是千篇一律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,像纪晓岚这种自命严谨的作者,恨不得每则笔记都道明出处,会不自觉地使用限制视角,也就会留下供读者想象的空白。这是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好处。而我有意识地改用一些新闻的写法,因为新闻可以选择从不同在场者的视角进入一个故事,也可以用口述实录的形式,这就让掌故的写法丰富起来。
到了《说史记》,我就在想:要不要有意识地再往前跨一步?掌故还是短小,适合一个截面或片段,有时不得不用“快进”的方式,也很难有细节的描写。如果写得再长一些,耐下心来慢慢进入人物与故事,或许能获得更多元的表达、更现场的感觉。
可是这样一来,难度何止倍增。因为这些故事本已经过了史书的锤炼与浓缩,仿佛一片新鲜的牛羊肉,已经风干日晒成可卷可藏、费牙费劲的肉纸,再要将它泡在水里,想复原成能炒能炸的肉片、肉丁,且不说能做到多高的还原度,水从何来?无非就是各种史料的拼合剔取,再就是作者的“历史想象力”了。
历史需不需要想象力?人言人殊。常常需要给别人讲一个道理:史料不是历史,对史料的阐述才是历史。一堆断烂朝报,要连缀拼接成一段看似完整的历史,想象力必然要参与其间。人们常说追寻历史真相,其实得到的只是某种对历史的解释,当然有高下精粗之别,但“真实”只是,用章太炎的话说,“古人之虚言”。
从这个角度上说,历史与小说,同属叙事,它们之间并没有一道不可跨越的藩篱。《史记》就是兼二者之美——这也是纪传体的特色,要写活人物,就不可能不运用文学的手法。即使是编年体,一字之择,片语之炼,写者的倾向自然就在其中,也就引导着读者看向他心中的历史图景。
读者可以只看文章好坏,管你历史还是小说。作者心中,不能没有原则。蝙蝠似禽似兽,但生物学上总会给它个定性。如果你来问我,我会说,我写的还是历史,只不过“用小说法,而以记史”。
《说史记》诸篇的叙事者大都是伪托的,但不等于书里的细节是编造的,可是我也不敢说每一个细节都经得起严格的推敲。我给自己定的原则大抵是:不编情节,对话和场景可以想象,但事件与情节必须有史料记述。《觉醒年代》的编剧说“大事不虚,小事不拘”,我写的历史,跟这部剧还是不太一样,小事我也拘,但是现场的氛围,确实只能依靠想象。
其实要分清叙事者是否伪托,非常容易,如果实有其人,他会有实在的姓名与身份,否则叙事者只是一个功能性的符号,代表着一种视角,亲历者、旁观者、听闻者……我想追寻的并非清晰的历史阐述,而恰恰是混沌难言的历史现场感,每个人都像瞎子摸象,只了解一部分事实——即使我们这些后世的人,又何尝知晓全部信息?所以这些篇什的目标,就是将近代史这个庞然大物放在一具单筒望远镜里观察,求其细不求其宏。
出于这个目的,我选择的叙事者,往往会是一些小人物,门房、丫鬟、学徒、闲人……最好用的,还是职在录事的记者。为了追寻鲜活的历史场景,我不惮于在想象中化身穿越者,用这种另类的方式贴近历史,再贴近一点。